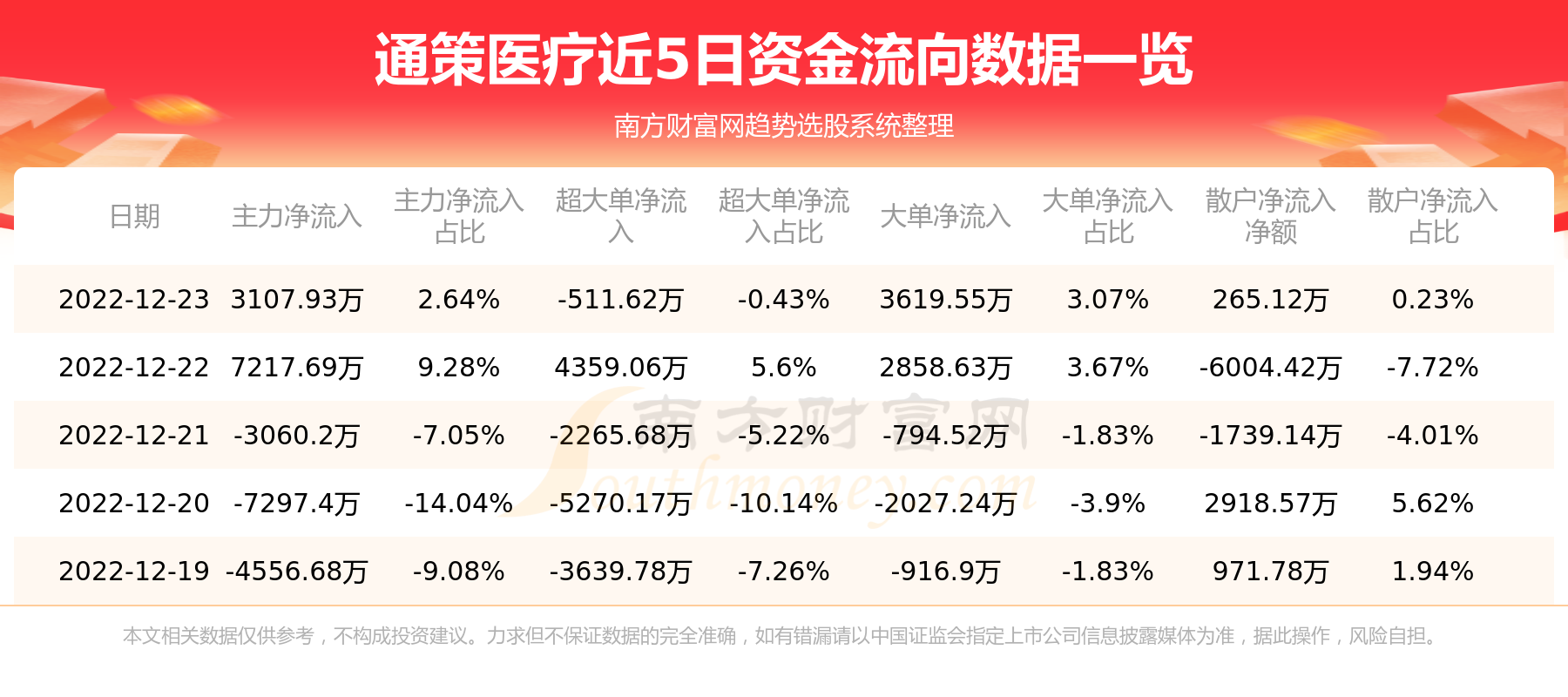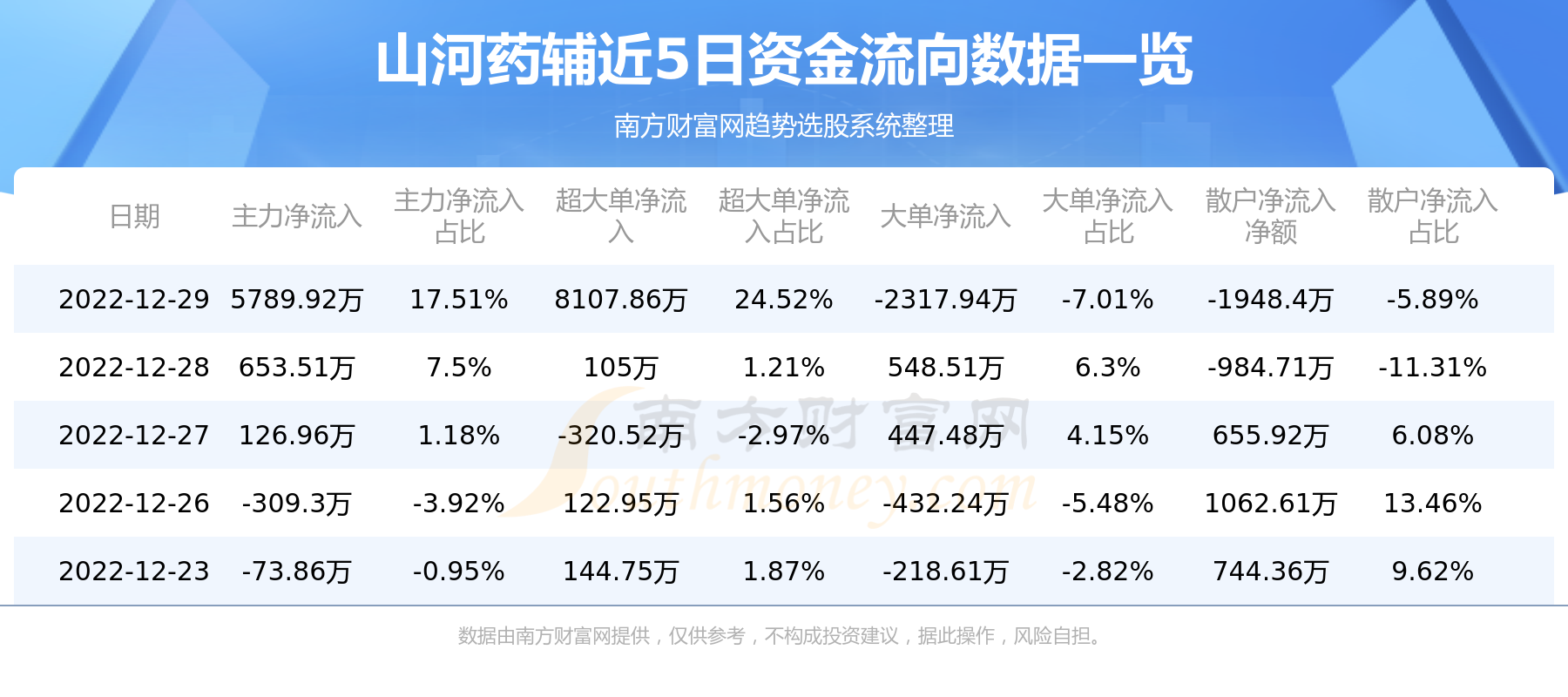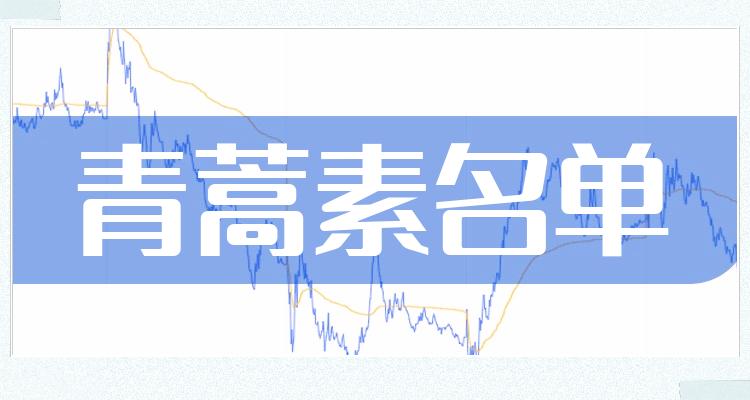作者 | 吴立元 肖立晟 罗朝阳
美国CPI在2022年3月突破8%,达到1982年以来最高水平,核心CPI也突破6%。虽然美联储已大幅加息并缩表,通胀依然表现出了很强的顽固性。当前,全球疫情形势依然复杂,叠加地缘危机,大宗商品价格与全球供应链压力较大,通胀形势依然充满不确定性。围绕美国通胀走势,存在着非常激烈的争论。美联储2022年9月21日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Summary of Economic Projections)显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的委员们认为美国2023年的个人消费开支价格指数(PCE)将降至3%以下,2024年将降至2.5%以下。萨默斯等人的研究则认为,现行的CPI统计方法低估了美国通胀,修正后的CPI已接近20世纪70年代,美国通胀形势极其严峻。更有分析认为,考虑到人口老龄化、地缘风险上升、逆全球化等供给侧因素,大缓和时代已经结束,高通胀时代即将到来。这不禁让人们想起了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以下简称“大通胀”)。那么,持续十几年的大通胀会重现吗?本文从工资物价螺旋与通胀预期形成机制的角度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尝试回答这一问题。
两轮通胀的相似之处
本轮通胀与20世纪70年代的大通胀有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也正是人们担忧再次出现类似滞胀的原因。概括而言,两轮通胀主要有三个重要而显著的相似点。
供给冲击都是通胀大幅上升的重要因素。供给冲击是两次通胀最为鲜明的特征,而供给冲击对通胀的影响是直接而剧烈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贸易逆差持续扩大,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美元与其他贸易顺差国家货币的汇率越来越难以维持。60年代到70年代初,美元对马克等非美货币显著贬值;1972年,连续两年的气候异常导致了全球粮食危机;1973年,欧佩克石油禁运带来第一次石油危机,全球油价大幅飙升;1979年,伊朗革命导致第二次石油危机,油价再次飙升;70年代初,尼克松实行价格管制。新冠肺炎疫情同样带来了巨大的综合性供给冲击,不仅能源和矿产等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普通消费品价格也因供应链、运输受到限制而全面涨价;叠加2022年3月以来的俄乌冲突,能源及粮食的价格上涨压力更是显著增大。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疫情大概率还要持续相当长时间,尤其是作为产品主要制造国的新兴市场国家;以俄乌冲突为代表的地缘政治危机也成为中长期问题。由此可见,在两轮通胀中,供给冲击不但非常剧烈,而且持续时间都比较长。
都经历了货币与财政的双重刺激。本轮疫情暴发以来与20世纪70年代,经济都出现了增速下台阶的现象,但政府仍然实施了大规模刺激政策,且都体现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双重刺激。约翰·肯尼迪于1961年上任后,提出“新边疆政策”,放松货币政策,并增加财政赤字,例如制定实施太空探索和登月计划、实施老年医疗保险、扩大对外援助等;约翰逊提出“伟大社会计划”,实施了一系列扩张性财政政策,越南战争又进一步增加了政府支出;尼克松也于1972连任之际大幅增加社会保障支出;疫情以来,美国也实施了大规模的货币宽松与财政刺激。从政府支出增速看,1966年一季度到1982年四季度,美国政府支出季度同比增速平均值高达10.8%。本次疫情以来(2020年二季度到2022年一季度),美国政府支出同比增速平均值高达12%。与上述时期形成对照,从1983年一季度到2020年一季度,美国政府支出同比增速平均值为5%。从货币供给增速看,1960—1970年的美国M2同比增速平均值为6.8%,而1971—1982年的M2同比增速为10%。2009—2019年,美国M2同比增速为6%,但疫情以来(2020年初至2022年一季度),M2同比增速平均值高达17.1%。
美联储政策都出现一定失误。大量对美联储议息会议历史资料的研究强调了美联储政策失误是大通胀产生的重要原因,认为美联储迟迟没有出台有效的反通胀政策的原因在于错误的思想。一方面,美联储估计的自然失业率远低于真实水平,这导致其错误地认为美国经济仍低于潜在水平,因而继续实施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另一方面,美联储认为通胀并非货币政策造成的,央行也难以控制通胀,而且对控制通胀的成本的估计过于悲观。后来的发展表明,正是沃尔克改变了这些思想,货币政策立场与大通胀的形势才得以改变。疫情以来,发生了与大通胀期间非常相似的情况。疫情后,美联储提升了对通胀的容忍度,而且在通胀初期一再强调通胀的暂时性,客观上纵容了通胀的上升。2021年8月,CPI同比增速已从2020年低于1%的低点上升至5%以上,远高于疫情前水平,鲍威尔仍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的讲话中认为通胀是不可持续的。
“工资—物价螺旋”及其形成条件
20世纪70年代,通胀快速攀升最终演变为“工资—物价”的螺旋上升。例如,1973—1982年,工资同比增速几乎都在8%以上;从1974年三季度开始,连续5个季度工资同比增速超过10%;1979年四季度到1981年一季度,工资连续6个季度同比增速超过10%。与此同时,通胀预期也持续攀升,走势几乎与通胀保持一致,形成了预期的自我实现及通胀的加速上升,如图1所示。总之,工资、物价、通胀预期三者的上升相互加强,形成了典型的“工资—物价”螺旋。

数据来源:CEIC、Wind
图1 1940年以来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速与工资增速走势
当物价上升时,工人的实际工资受到侵蚀;当工资上升超过生产率增速时,企业利润受到侵蚀。“工资—物价螺旋”产生的核心机制是,工人为保护其实际工资而要求涨工资,企业为保护其利润而提价。两者相互加强,推动通胀预期上升,进而形成通胀预期的自我实现,导致通胀加速上升。从上述机制可以看出,“工资—物价螺旋”产生的基本条件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工资上涨速度持续超过劳动生产率。此时企业的实际成本上升,利润会受到侵蚀,产生涨价压力。第二,工人具有较强的工资谈判力。当其实际工资受到侵蚀时,工人能有效迫使雇主提升工资。第三,企业与工人形成更高的通胀预期。有两个重要因素可能导致这一现象发生:一是供给冲击较为严重且持续过长时间导致人们走出低通胀惯性区间;二是央行纵容通胀,公众不再相信央行有稳定通胀的决心。
当前与大通胀时期存在关键差异
本轮通胀与大通胀虽然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存在更多的差异,尤其是上述工资物价螺旋形成的条件在本轮通胀中并不具备。
疫情冲击下生产率与工资变动尚未发生重大偏离
图2比较了20世纪70年代与当前美国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差异。可以看出,20世纪70年代的大通胀期间,美国工人的工资增速大幅上升,而生产率增速却显著下降,二者差异不断扩大。2020年疫情以来,美国工人的工资增速虽然快速上升,但生产率增速也在同步增长,二者间的差异并未显著扩大。也就是说,20世纪70年代美国大通胀期间,企业面对工资支出持续上升,工人的单位产出却不断下降,因此出现强烈的提价动机,触发“工资—物价”螺旋上升机制,市场通胀预期不断上涨。2020年疫情暴发后,虽然美国国内的企业工资成本快速上升,但工人单位产出的生产率也在迅速上涨,缓解了一部分通胀压力,中长期的通胀预期基本稳定。

数据来源: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图2 1971年以来美国通胀水平、通胀预期与工资增长率变动情况
此外,还有两个证据可进一步证实近来的价格上升仍处于疫情导致的供给不足层面,尚未演化为需求带动的“工资—价格”相互推升。第一,疫情以来,虽然美国通胀与工资均上升较快,但分解来看,物价上涨最快的制造业的工资上涨却较慢,而工资上涨较快的服务业的物价上涨却较慢。这表明,物价与工资之间尚未形成显著的螺旋上升关系。第二,近期工资增长最快的零售、运输仓储、教育医疗及休闲酒店行业在疫情前(2009—2019年)的10年几何平均同比增速分别为2.5%、1.9%、2.2%和2.5%,并未显著快于2%的制造业平均工资增速。截至2021年6月,两年的通胀几何平均同比增速分别为5.7%、4.2%、5.1%和6.8%,显著快于制造业的3.8%,这进一步表明,近来服务业工资的上涨受疫情影响较大,并非需求冲击所主导。
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导致工人议价能力下降
工人议价能力是工资物价螺旋形成的重要条件。在20世纪70年代大通胀时期,工资增速常常达到10%以上,成为导致“工资—物价”螺旋上升的重要推动力,这与当时劳动力市场结构密切相关。大通胀后,美国劳动力市场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导致工人议价能力显著下降,其中两个最鲜明的变化表现在工会势力与就业的行业结构。
一方面,美国工会势力已经大幅减弱。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美国工会推动进行高达两位数的加薪幅度来应对接近8%的通货膨胀,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美国经济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并终结了充分就业趋势。当前劳动力市场结构与20世纪70年代已经大不相同。当时工会劳动力占到总劳动的四分之一,如今只占十分之一左右,这意味着工人的谈判力显著下降。近期通胀飙升而实际工资显著下降鲜明地反映出了这一点。野口悠纪雄在《战后日本经济史》一书中也强调,日本在石油危机中通胀压力显著较小的重要原因是日本的工会与美欧显著不同。日本工会大多设立在公司内部,工人与公司有利益与共的特征,因而未强烈要求涨工资,这从反面证实了这一观点。

数据来源:CEIC
注:高工资行业包括专业和商业服务业,信息服务业,金融、保险、房地产租赁业以及采掘业;中工资行业包括制造业和建筑业;低工资行业包括艺术、娱乐、休闲、住宿和餐饮,教育、健康与社会援助业,贸易、运输和公共事业以及其他服务业
图3 1970年以来美国就业的行业结构变化
另一方面,美国中高工资行业就业占比显著下降,而低工资行业就业占比大幅上升。如图3所示,20世纪70年代前,美国就业的行业结构变化较为缓慢,制造业就业与服务业就业占比变化相对较小;20世纪70年代后,制造业就业占比快速下降而服务业就业占比快速上升,美国服务业占非农就业的比重从1980年的66%上升至目前的80%以上。与此同时,高工资行业就业占比小幅缓慢上升,中等工资行业就业占比大幅下降,低工资行业就业占比大幅上升。因此,从行业层面看,美国就业中服务业就业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且工资较低的服务行业就业增速明显快于工资较高的行业。总体来说,工资较低的工人议价能力较低,因此这些结构变化大大降低了整个经济中工人的工资议价能力,抑制了从价格到工资的传导,降低了“工资—物价螺旋”产生的可能性。
美联储货币政策发生重大变化
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美联储货币政策从思想到框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里有三点值得强调。
第一,20世纪70年代,美联储没有对通胀目标作出明确承诺,且当时美联储对产出增长更加重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传统凯恩斯主义思想成为当时宏观经济政策的绝对主流。美联储信奉菲利普斯曲线,认为央行可以在通胀率和失业率之间进行较为自由的权衡取舍,没有意识到可能出现通胀率与失业率均很高的滞胀情形。八九十年代后,随着经济理论与政策实践的发展,通胀目标制逐渐成为央行货币政策的指导思想。纳尔逊(Nelson,2005)估计了1966—1995年美国的货币政策规则,发现1966—1979年,利率对通胀率反应系数显著小于1,而对产出反应系数较大;1980—1995年利率对通胀率反应系数大幅提升,显著大于1,这从数量上证实了美联储货币政策框架的变化。
第二,20世纪70年代,美联储对通胀持有非货币主义观点。当时的美联储倾向于认为,通胀上升是石油价格冲击等其他因素造成的,而不是货币政策造成的。这一观点的推论是,央行难以控制通胀。通胀的货币主义观点则认为,通胀是货币现象,成本推动冲击是暂时的,只会影响当前通胀,并不影响长期通胀与通胀预期,通胀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货币政策没有将总需求调整到潜在产出水平,从而导致产出缺口上升。
第三,美联储与美国政府都在吸取20世纪70年代的教训。如今美联储已经意识到通胀并非是暂时的,并开始采取紧缩政策,总体仍在实施其货币政策框架的承诺,这明显有利于控制通胀预期,从预期源头上阻止“工资—物价螺旋”的产生。美联储于2021年底开始快速转变过去通胀是暂时的观念,不断强调通胀具有明显的持续性。2022年,美联储已连续加息6次,累计加息375基点,并于6月开始启动缩表。虽然美联储一开始低估了通胀的持续性,行动较为迟缓,但这些紧缩货币政策动作还是表明,美联储已经意识到通胀问题的严重性,并采取实际行动遵守其货币政策框架。与此同时,虽然当前美国经济衰退风险相当大,甚至已经开始衰退,但美国政府仍表示对反通胀的支持。例如,2022年5月30日,拜登在华尔街日报刊登《我的抗通胀计划》的文章,表示将支持美联储通过减少经济需求来抑制高通胀的努力,并强调不会干预美联储。
结论与展望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工资—物价螺旋”形成的条件在本轮通胀中并不具备。企业并未面临工资上涨造成的巨大利润压力,工人的工资议价能力也已经显著下降,美联储与美国政府都将通胀视为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愿意承受一定程度的经济衰退。这些变化将使本轮通胀的治理难度显著低于20世纪70年代。接连不断的供给冲击仍是人们担忧的主要风险,如能源价格与供应链压力,这的确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但是,似乎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供给会持续恶化下去。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能源与食品在生产和消费中的份额已明显下降,美国本身的能源生产能力大幅增强,美国高通胀的同时伴随着美元的升值也不同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时的美元贬值,降低了进口价格上升压力。在美联储乃至全球普遍紧缩的背景下,全球性增长放缓乃至衰退会大幅抑制能源需求,能源价格虽然还会波动,但持续上涨似乎也缺乏基础。对于供应量紧张状况,纽约联储统计的全球供应链压力指数(GSCPI)是一个较好的观察指标。该指标显示,疫情暴发后,全球供应链面临的压力快速上升,到2020年4月达到阶段顶点后快速下跌,从2020年10月开始再次持续攀升,到2021年12月再创新高,之后震荡下行,截至2022年5月已低于2020年4月的阶段高点。对华关税方面,美国最近也在考虑是否取消部分或全部关税。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尽管我们仍应对这些供给变量谨慎观察,但其逐步衰减的可能性显著大于恶化的可能性。